雨水像银针般刺入我的皮肤。
我蜷缩在长途大巴最后一排,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
窗外是陌生的沿海城市,霓虹灯在雨幕中晕染成血色光斑。
十八年来第一次离开山村,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临行前帮母亲剥蒜时沾上的泥土味。
"小菊妹子,前面就到了。
"邻座的中年女人第五次检查我的车票,她自称王姨,是城里服装厂的人事主管,"咱们厂包吃包住,月薪六千,你这样的好苗子干得好还能当领舞呢。
"我捏紧印着"金太阳服装有限公司"的招聘简章,上面烫金的舞者剪影在昏暗车厢里微微发亮。
三天前这纸传单飘进我们那个连快递都不送的穷山沟时,全村人都说是我死去的爹在保佑我。
大巴突然急刹,我的额头重重磕在前座椅背上。
王姨拽着我的手腕站起来:"到了到了!
"她手劲大得惊人,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
雨下得更大了。
我们站在一个废弃工业区门口,铁门上的"金太阳"招牌己经锈蚀得只剩"日"字还勉强可辨。
远处闪电劈开云层,照亮厂区内杂草丛生的空地和一排排黑洞洞的窗户。
"王姨,这不像..."我话音未落,后脑勺突然挨了重重一击。
天旋地转中,我看见王姨正在和一个穿黑雨衣的男人交接什么,那男人塞给她一叠钞票,她数钱时嘴角咧到耳根。
水泥地的寒意透过单薄的连衣裙刺入骨髓。
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却被雨靴踩住手腕。
黑雨衣蹲下来,掀开兜帽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左眉骨有道疤,右耳戴着枚金貔貅耳钉。
"常少要验货。
"他扯开我的衣领,粗糙的手指在锁骨上游走,"确实是雏儿。
"我被拖进厂房时,鞋跟刮掉了左脚的运动鞋。
雨水混着铁锈味的空气灌进肺部,远处传来柴油发电机的轰鸣。
走廊尽头亮着盏频闪的应急灯,紫白光线下堆满霉变的布料捆。
"求求你..."我嗓子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我可以干活,什么活都..."黑雨衣突然把我推进一个房间。
霉味瞬间被古龙水的气味覆盖,三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被改装成临时休息室,真皮沙发旁站着个穿丝绸睡袍的男人。
他正在往水晶杯里倒洋酒,手腕上的百达翡丽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抬头。
"他说。
我牙齿打颤着抬起脸。
这是个西十岁左右的男人,皮肤黝黑得像常年出海的老渔民,但186cm的健壮身材裹在睡袍里,像头披着绸缎的熊。
他左肩的虎头刺青从敞开的领口探出来,琥珀色的眼珠正盯着我。
"常、常总好..."我下意识用招聘简章上的称呼,膝盖一软跪在了地毯上,"我会跳舞,还会..."名叫常大强的男人突然捏住我的下巴。
他手指有淡淡的雪茄味,力道大得让我听见自己颌骨咯咯作响。
"王翠花没骗我,确实水灵。
"他拇指抹过我嘴唇,"知道为什么选你吗?
"我摇头时眼泪甩在他手背上。
常大强突然笑了,露出两颗镶金的犬齿:"因为你们村没通网。
"他松开我,从抽屉里拿出个黑色皮箱,"二十万,买你一辈子闭嘴。
"窗外炸响的惊雷淹没了我的尖叫。
常大强单手就撕开了我的连衣裙,纽扣崩飞时有一颗打在我眼角。
我拼命去抓茶几上的酒瓶,却被他掐着脖子按在落地窗前。
雨水在玻璃外扭曲成泪河,倒映出他压下来的黑影。
"看清楚。
"他咬着我耳垂说,"记住是谁开的苞。
"剧痛袭来时,我咬破了嘴唇。
血锈味在口腔蔓延,常大强左肩的虎头刺青随着他的动作在我眼前晃动。
琥珀色的虎眼在闪电中忽明忽暗,像两盏通往地狱的灯。
我盯着那刺青,指甲在玻璃上刮出刺耳的声音。
暴雨冲刷着玻璃,也冲刷着他留在我体内的污秽。
常大强提起睡裤时,我正盯着地毯上那只孤零零的运动鞋——粉色的鞋面沾了血,是我考上县高中时母亲咬牙买的礼物。
"明天有人送你去别墅。
"他系着皮带,用鞋尖挑起我下巴,"敢报警,就把你妈卖到缅甸窑子。
"我蜷缩着去够那只鞋,却被他踩住手指。
"听说你会跳舞?
"常大强碾着我的指骨,"下周我生日宴,跳个一字马助兴。
"他大笑着把酒杯里的残酒倒在我背上,冰凉的液体顺着脊椎流进伤口。
脚步声远去后,我爬到墙角呕吐。
胆汁混着血丝溅在墙皮剥落的裂缝上,那裂缝形状像极了我老家后山的断崖。
闪电再次亮起时,我看见办公桌下有把美工刀。
我攥着刀片爬向茶几,常大强落下的打火机旁边有张合影。
照片里他搂着个穿高中制服的少年站在游艇上,少年颈间挂着和我包里一模一样的玉坠——那是我们村后山特产的蓝田玉,全乡只有李石匠家会雕这种貔貅纹样。
发电机的噪音突然停了。
黑暗中,我摸到常大强忘在沙发上的手机,锁屏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合照,背景是"常氏纺织二十周年庆典"。
照片角落的日期显示这是三天前拍的,定位在宁波香格里拉酒店。
雨声渐小时,我用染血的裙摆包好手机、照片和美工刀。
穿回那只脏兮兮的运动鞋时,发现鞋底沾了块碎玻璃——是从常大强摔碎的酒杯上崩出来的,棱角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像颗微型钻石。
我把它藏进了鞋垫夹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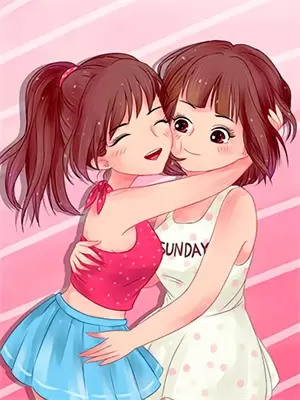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