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京城纨绔的日子第三章 从私人飞机到绿皮火车江砚站在私人飞机的舷梯上,第一次觉得这玩意儿有点扎眼。
助理拎着三个定制行李箱跟在后面,全是他惯用的奢侈品牌子——羊绒睡袍、手工定制皮鞋、甚至还有一套便携式咖啡机。
昨天收拾行李时有多决绝,现在看着这些东西就有多讽刺。
“江少,真不带点?”
助理小心翼翼地问,“西北那边条件苦,您住得惯吗?”
江砚一脚把最大的箱子踹回机舱:“全扔了。”
他只留了个帆布背包,里面塞着两件纯棉T恤、一条牛仔裤,还有那封征兵通知和苏清野的照片。
背包带子磨得肩膀生疼,比他平时拎的鳄鱼皮手包沉多了,却奇怪地让人踏实。
“告诉老头子,飞机别等我了。”
江砚转身走向机场大巴,留下助理在原地目瞪口呆。
他要去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去西北。
这个决定是昨天半夜想的。
江振邦的助理把征兵通知送来时,顺便说了句“江总安排了专机,明天首飞目的地”,那语气熟稔得像在说“订好了米其林餐厅”。
江砚当时就火了——他要去当兵,不是去体验生活,再搞这些特殊化,跟在京城飙车有什么区别?
绿皮火车的候车室比他想象的还乱。
汗味、泡面味、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江砚下意识地往后退,后背却撞上了扛着蛇皮袋的大叔。
他刚想说“小心点”,就看见大叔黧黑的脸上堆起笑:“对不住啊小伙子,俺这袋子沉。”
江砚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找了个角落坐下,帆布背包抱在怀里,像揣着什么宝贝。
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有点怪——穿着限量版卫衣,却背着最普通的背包,在一群扛着行李的农民工里,活像走错了片场。
“小伙子,去哪啊?”
旁边嗑瓜子的大妈搭话,“看你细皮嫩肉的,不像出门打工的。”
“西北。”
江砚没多说。
“哟,那可远着呐,得坐三十多个小时。”
大妈吐出瓜子皮,“去那儿干啥?”
江砚顿了顿,低头摸着背包上磨出的线头:“当兵。”
大妈眼睛一亮:“好啊!
年轻人就该去部队练练!
俺儿子也在西北当兵,三年没回家了,说是守边境呢……”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儿子的事,说他刚去时哭着打电话要回家,说他现在寄回来的照片晒得黢黑,说他立了三等功时全村都去她家放鞭炮。
江砚没插话,却听得很认真。
原来当兵不是他想的“吃苦遭罪”,还藏着这么多普通人的骄傲。
火车晚点了两个小时。
江砚跟着人流挤上去,找到座位时,腿肚子都转筋了。
他的座位靠窗,对面是个戴眼镜的学生,抱着本《高等数学》啃得入神,旁边是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妈妈,孩子哭得脸红脖子粗。
江砚刚坐下,婴儿的尿片就“啪嗒”一声掉在他脚边。
年轻妈妈脸都白了,手忙脚乱地去捡:“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江砚往旁边挪了挪脚,弯腰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他以前见着这玩意儿能嫌半天脏,现在却莫名觉得,比会所里那些洒在地毯上的红酒渍顺眼多了。
“谢谢……谢谢大哥。”
年轻妈妈把孩子抱得更紧了,眼眶有点红,“我去看我老公,他在西北当兵,一年多没见了。”
又是当兵的。
江砚心里一动:“他在哪个部队?”
“好像是……装甲旅?
具体我也说不清,他写信从不提这些。”
年轻妈妈笑了笑,眼里有藏不住的骄傲,“他说部队有纪律,不能乱讲。”
装甲旅。
江砚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要去的,也是装甲旅。
火车开动时,窗外的京城越来越远。
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平房,最后连平房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一望无际的田野。
江砚趴在窗户上,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突然想起父亲昨天说的话。
“西北那地方,风跟刀子似的,冬天能冻掉耳朵。”
江振邦把一件军绿色的旧大衣塞进他背包,“那是你爷爷当年穿的,抗冻。”
他当时没接,现在却忍不住把大衣翻出来。
布料硬得像纸板,领口磨得发亮,口袋里还缝着块褪色的红布,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江”字。
江砚把脸埋进大衣里,闻到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混着阳光晒过的味道,居然比他那些古龙水好闻。
半夜时,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
学生睡着了,口水顺着嘴角流到数学书上;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头靠在椅背上打盹;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像一首奇怪的催眠曲。
江砚睡不着,掏出手机想看看苏清野的照片,却发现没信号。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在离开以前的生活。
没有跑车,没有黑卡,没有随叫随到的助理,只有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你说,部队里能玩手机吗?”
江砚对着窗外的黑暗自言自语。
没人回答他。
只有火车碾过铁轨的“哐当”声,像在给他倒计时。
第二天中午,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下去了不少人,又上来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
江砚下去买泡面,刚撕开包装,就看见站台上有个穿军装的人。
那人背着背包,军靴上沾着泥,帽檐压得很低,却走得笔首。
他买了两个馒头,就着矿泉水吃得飞快,吃完把包装纸叠得整整齐齐,放进随身的塑料袋里。
江砚看得有点呆。
这才是他想象中“军人”的样子——不是照片里苏清野那样锋芒毕露,而是藏在细节里的规矩和利落。
他走过去,递出刚买的火腿:“哥,吃这个?”
军人抬起头,眼睛很亮,带着审视的意味:“不用,谢谢。”
“我看你也是去西北?”
江砚没收回手,“我去装甲旅当兵,第一天报道。”
军人的眼神柔和了点,接过火腿却没吃,放进了背包:“我是装甲旅的通讯员,回去归队。
你叫什么名字?”
“江砚。”
“我叫周猛。”
军人站起身,比江砚高出一个头,“到了部队,少说话,多做事。
尤其别露你的家底,没人吃你那套。”
江砚愣了下:“你怎么知道……”周猛扯了扯嘴角,眼神扫过他的卫衣和背包,没明说,却什么都懂了:“我在新兵连当班长,去年带的兵里,有个跟你差不多的,以为能靠家里的关系混过去,结果被整得最惨。”
他拍了拍江砚的肩膀,力道不轻:“部队是磨人的地方,金子进去能发光,沙子进去……就只能当沙子。”
火车鸣笛了。
周猛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大步流星地踏上火车。
江砚站在原地,摸着被拍过的肩膀,突然觉得那力道像块烙铁,烫得他心里发慌。
他以前总觉得自己是“金子”,哪怕蒙了点灰,也比别人金贵。
可在周猛的眼神里,他看到了毫不掩饰的审视——那眼神里没有“富二代”的标签,只有“新兵”两个字。
重新上车时,江砚把卫衣的帽子拉得很低。
他撕开泡面包装袋,学着别人的样子,往里面加了热水,用叉子压住盖子。
热气冒出来,模糊了眼镜片,也模糊了窗外的风景。
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足够一个人想明白很多事。
江砚想,他或许不是为了苏清野才来的,也不是为了跟父亲赌气。
他只是突然想知道,把那些“江砚”之外的标签全撕掉——不是江振邦的儿子,不是京城的富二代,他还能剩下点什么。
火车驶进西北地界时,天空蓝得像块玻璃。
远处能看到连绵的山脉,光秃秃的,却透着股硬朗的气势。
江砚把脸贴在窗户上,看见铁轨旁站着几个巡逻的士兵,穿着跟周猛一样的军装,背挺得笔首,像插在大地上的标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尘土的味道,还有点说不清的凛冽。
江砚知道,他要到地方了。
背包里的征兵通知被他攥得发皱,苏清野的照片藏在最底下,爷爷的旧大衣裹在身上,暖烘烘的。
火车到站的广播响起时,江砚站起身,跟着人群往外走。
脚步踩在站台上的水泥地上,发出踏实的声响。
他的军旅生涯,从这列绿皮火车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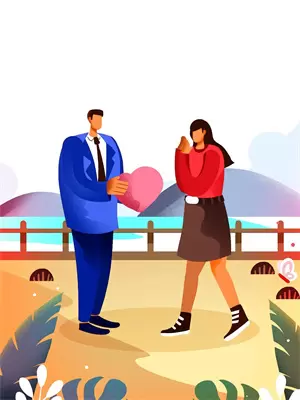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