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热的风裹着河腥气砸在脸上时,陈默正把最后一口生鱼塞进嘴里。
牙齿咬破鱼皮的瞬间,他看见竹楼外的湄公河泛着灰绿色的光,像一条藏着毒牙的巨蟒。
“阿默,发什么呆?”
旁边的刀疤脸用刀柄撞了撞他的胳膊,“坤沙哥让你过去。”
陈默低下头,用袖口擦了擦嘴角的血渍。
刀疤脸是“山猫”的人,三天前在边境的丛林里见到他时,他正被野狗追得只剩半条命。
那时他叫“阿默”,一个据说是从云南逃荒来的流浪汉,左臂上有一道假的烟疤——那是用烙铁在自己胳膊上烫出来的,结痂时疼得他整夜咬着木棍发抖。
竹楼里弥漫着鸦片和汗臭的混合气味。
坤沙坐在虎皮椅上,手指上的金戒指在煤油灯下发亮,他身后的木柱绑着个男人,裤腿浸在血泊里,苍蝇正围着伤口打转。
“听说你懂汉语?”
坤沙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
陈默猛地绷紧后背。
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在这片金三角腹地,懂汉语的人要么是被通缉的逃犯,要么是警察的探子。
他故意让眼神晃了晃,露出恰到好处的怯懦:“小时候……跟镇上的汉人学过几句。”
“那就好。”
坤沙笑了,露出黑黄的牙,“昨天抓了个‘货’,说的话没人懂,你去问问,他是不是‘穿制服的’。”
陈默的指甲掐进掌心。
被绑的男人抬起头,额角的伤口让他半眯着眼,可那双眼睛里的光却像淬了火的钢针——那是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有的眼神。
陈默忽然想起出发前,局长老周拍着他肩膀说的话:“到了那边,看见任何熟人,都当不认识。”
他走过去,蹲在男人面前。
男人的嘴唇动了动,用极低的声音说:“代号‘夜莺’,任务失败……”陈默的心脏骤然缩紧。
夜莺是公安部安插在坤沙集团的卧底,三个月前失去联系,没想到……他猛地抬手,一巴掌扇在男人脸上,声音陡然变粗:“坤沙哥问你话,装什么哑巴!”
男人愣住了,随即眼中涌起暴怒,一口血沫啐在陈默脸上:“狗汉奸!
你会不得好死!”
“看来是个硬骨头。”
坤沙站起身,从腰间抽出匕首,“阿默,给你个机会——他要是警察,就捅死他。”
匕首扔在陈默脚边,金属反光刺得他眼睛发疼。
他看见男人的喉结在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死死盯着他,眼神里有恨,还有一丝……解脱?
竹楼里的人都在笑,刀疤脸吹了声口哨:“新来的,不敢了?”
陈默捡起匕首,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想起警校的射击课,老周教他们:“枪是保护人民的,不是杀人的。”
可现在,他握着的刀,却要刺向自己的同志。
他走到男人身后,匕首的尖端抵住对方的后心。
男人忽然笑了,声音嘶哑:“记住……毒贩的孩子,也会被他们当‘货’卖……”陈默闭上眼,猛地用力。
温热的血溅在他手背上,像岩浆一样烫。
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得像破风箱,而周围的哄笑声里,坤沙拍了拍他的肩膀:“不错,够狠。
从今天起,你跟着我。”
深夜的丛林里,陈默靠着树干呕吐。
胃里的生鱼和胆汁一起涌出来,他却像感觉不到恶心,只是反复搓着手背上的血迹,可那腥气仿佛渗进了骨头里。
裤兜里的卫星电话震动了一下,是老周的加密信息:“身份己从系统抹去,此后,世上再无陈默。”
他望着湄公河的方向,那里的黑暗浓得化不开。
他知道,从刺出那一刀开始,“陈默”己经死了。
活下来的“阿默”,要在地狱里走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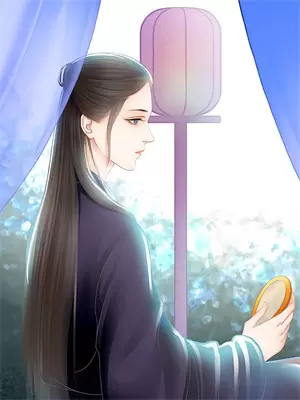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