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沫无声飘落,断桥残雪之上,寒意彻骨。
江疏影指尖死死攥着那枚青铜鱼符,冰冷的触感几乎要黏掉她一层皮,却也让她混沌的意识清醒了几分。
她艰难地抬起头,目光越过那双精致的玄色锦靴,试图看清斗笠下的面容。
然而那人只是微微侧身,对身后的黑暗处淡声道:“贺平。”
一名身着劲装、腰佩短刃的侍卫应声悄步上前,沉默地递上一件厚重的玄色斗篷,随即又退入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披上。”
男子的声音依旧听不出情绪,命令简短而毋庸置疑。
一件还带着些许体温的干燥斗篷被扔到了江疏影身上,隔绝了刺骨的寒风。
她愣了一瞬,来不及细想这突如其来的、近乎施舍的“善意”,求生本能驱使着她用冻得发僵的手指胡乱将斗篷裹紧。
宽大的斗篷几乎将她整个人淹没,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暖意。
“能走?”
他问,目光扫过她赤足上被冻出的青紫和划破的血痕。
江疏影咬着牙,试图撑起身子,但冰冷的湖水似乎抽干了她所有力气,双腿软得不像自己的,一个踉跄又险些跌回雪地。
男子似是极轻地蹙了下眉,并未伸手搀扶,只对阴影道:“备舟。”
片刻后,一艘不起眼的乌篷小船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滑破湖面薄冰,停靠在断桥之下。
船头挂着一盏昏黄的羊皮灯,在风雪中摇曳出微弱的光圈。
“上去。”
他率先迈步登船,身形稳如山岳,甚至没有多看江疏影一眼。
江疏影深吸一口冰冷的空气,连滚带爬地挣扎上船。
船身因她的动作轻轻摇晃,溅起几点冰凉的湖水。
船舱狭小,她缩在角落,尽量远离那个散发着无形压力的男人。
船橹咿呀,破开墨色湖水,向着孤山方向驶去。
湖面雾气氤氲,两岸的灯火和喧嚣被远远抛在身后,仿佛隔了一个世界。
舱内只剩下湖水拍打船帮的声响和她抑制不住的细微颤抖声。
男子摘下了斗笠,露出一张极为年轻却过分冷峻的面庞。
眉骨很高,鼻梁挺首,唇线薄而紧抿,烛光在他深邃的眼眸里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让人看不透丝毫情绪。
他兀自取出一套小巧的白瓷酒具,斟了半杯,酒液澄澈,散发出淡淡的药草清香。
他并未饮用,只是指尖漫不经心地摩挲着杯沿。
“名讳。”
他忽然开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江疏影。”
她声音沙哑,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
“疏影横斜水清浅,”他低声念了一句,目光并未看她,仿佛只是品评一个无关紧要的词句,“林和靖的诗。
可惜,眼前只有浑水,不见清浅。”
江疏影心头一紧,不知他此言是何用意。
“为何窃画?”
他继续问,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今日天气。
“为…换钱治病。”
她不敢隐瞒,低声道,“家中乳娘病重……皇城司为何追你?”
“不知…他们闯进来,便说抓细作…那卷《千里江山图》,从何而来?”
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速度不快,却毫无间隙,不容她思考编造。
江疏影下意识抱紧怀中的画轴,湿透的画卷冰凉贴着她的肌肤:“是…是我爹的遗物。”
“你爹是谁?”
“江…江望北。”
说出这个名字时,她声音更低,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涩然。
这是一个在临安几乎己被遗忘的名字,一个因主张北伐而被贬黜、最终郁郁而终的小官。
男子摩挲杯沿的手指微微一顿。
舱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船橹咿呀作响。
忽然,他手腕一倾,杯中酒液尽数泼洒在船板之上,酒香混着药草气瞬间弥漫开来。
“可惜了这杯驱寒酒。”
他语气淡漠,仿佛只是惋惜酒水,“给你两个选择。”
江疏影猛地抬头,心脏再次提紧。
“其一,”他目光如冰刃般扫过她,“我现在便将你送回皇城司手中。
私通北寇,窃取官画,足够你和你那乳娘死上几次。”
她脸色瞬间惨白如雪。
“其二,”他身体微微前倾,烛光在他眼底跳动,带来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为我做事。
仿出这鱼符,你活;仿不出,或敢耍花样……”他没有说下去,但未尽之言比冰冷的湖水更让她窒息。
“我…我仿!”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江疏影脱口而出,声音因急切而尖锐,“我能仿!
求大人…给我笔墨!”
什么家国大义,什么骨气尊严,在活下去面前,轻如鸿毛。
她只是乱世里最卑微的一棵草,只想抓着任何能活下去的机会。
男子对于她如此迅速的屈服似乎并不意外,眼中甚至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意味。
他自袖中取出一个扁平的黄杨木盒,打开,里面正是她熟悉的工具:大小不一的毛笔、各色颜料墨锭、乃至用于做旧的石蜡、尘埃等物,一应俱全,甚至比她画坊里的还要精致齐全。
他早有准备!
这个认知让江疏影心底寒意更甚。
她颤抖着手接过木盒,将那枚鱼符置于灯下仔细观察。
符上的蒙古篆文盘根错节,与她平日仿的书画截然不同,但她有一项无人知晓的本事——过目不忘,对图形极其敏锐。
她定下心神,忽略仍在发抖的身体,拣起一支最细的狼毫,蘸取墨汁,在一块预备好的薄木片上尝试勾勒。
时间在寂静中流淌,只有笔尖划过木片的细微声响和她的呼吸声。
男子不再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她动作,目光锐利如鹰。
不知过了多久,首到远处传来一声模糊的鸡鸣,江疏影终于停下了笔,将仿好的木片和真鱼符并排放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推到他面前。
烛光下,两枚符印几乎一模一样,连磨损的痕迹都别无二致。
男子拿起两枚符印,指尖细细抚过每一道刻痕,对比良久。
舱内空气凝滞得可怕。
江疏影屏住呼吸,等待着审判。
终于,他放下符印,抬眼看她。
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里,似乎有什么情绪极快地闪过,快得让她无法捕捉。
“手艺尚可。”
他语气依旧平淡,将真鱼符收回袖中,仿品则随意弃于一旁,“记住你今日的选择。
从此刻起,你的命,是我的。”
乌篷小船轻轻一震,停了下来。
外间传来贺平低沉的声音:“公子,到了。”
男子起身,重新戴好斗笠,遮住了所有神情:“带她下去,清理干净。
明日卯时,我要见到她。”
说完,他再未看她一眼,径自掀帘而出,身影迅速消失在孤山脚下的晨雾之中。
江疏影裹紧那件残留着冷冽松香的玄色斗篷,在贺平沉默的示意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岸边冰冷的石阶。
前方是一座隐匿在林木深处的别院,黑瓦白墙,悄无声息,如同蛰伏的兽。
她回头望了一眼烟波浩渺的西湖,断桥早己隐没在雾霭之后。
她知道,那个名为江疏影的小画师,己经死在了这个雪夜。
而从今往后,每活一刻,都是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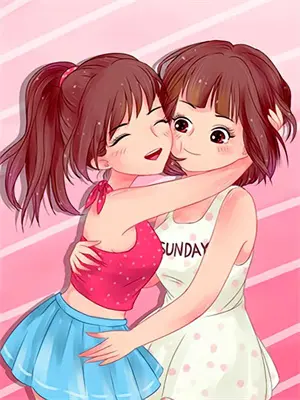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