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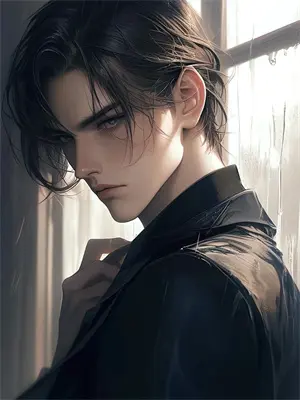
其它小说连载
小说叫做《万家灯火一盏不灭》是作者潘西来的小内容精选:第一盏灯的重量芮啸天调到文化馆那天上下着小不但能湿他穿了双新皮黑擦得能照出人这鞋是他特意买为的就是第一天上班有个好形结果刚进大一脚踩进一个水那坑不也就三厘可偏偏就那么水顺着鞋帮子灌了进他低头鞋面还亮脚底下却咕叽咕叽他没骂也没跳就站在那像根电线杆门卫老张从传达室探出头来:“新来的?走中间水泥别走两边...
主角:秦芳舒,芮啸天 更新:2025-09-28 07:22:07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第一章 一盏灯的重量芮啸天调到文化馆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不大,但能湿鞋。
他穿了双新皮鞋,黑色,擦得能照出人影。这鞋是他特意买的,
为的就是第一天上班有个好形象。结果刚进大门,一脚踩进一个水坑。那坑不深,
也就三厘米,可偏偏就那么巧,水顺着鞋帮子灌了进去。他低头看,鞋面还亮着,
脚底下却咕叽咕叽响。他没骂人,也没跳脚,就站在那儿,像根电线杆子。
门卫老张从传达室探出头来:“新来的?走中间水泥道,别走两边儿。”芮啸天点点头,
没说话,往里走。鞋子里的水一路挤,一步一个印子,像在写日记。文化馆是老楼,
五十年代盖的,墙皮掉得像头皮屑。走廊里一股霉味,混着陈年纸张的酸气。他分在资料室,
主任姓李,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时总爱把“格局”两个字挂在嘴边。
“小芮啊,你这学历高,北大的,咱们这儿正缺你这样有格局的人。
”芮啸天说:“我就是来干活的。”李主任笑了:“干活也得讲格局嘛。
”资料室在一楼最里面,窗户对着后院的垃圾堆。他坐下,打开档案柜,
第一本抽出来的是《延津县文化志1983-1985》。书页发黄,边角卷着,
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本志由原文化馆馆长秦明远主编。”再翻,夹着一张纸条,
字迹潦草:“永远不要吹灭别人的灯。——秦明远”芮啸天把纸条看了三遍,没明白啥意思。
他想,这老头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灯还能吹灭?那得是蜡烛吧?现在都电灯了,吹个屁。
中午吃饭,他在食堂碰见一个女的,穿件灰蓝色外套,饭盆里是白菜炖粉条,没肉。
她坐角落,低头吃,吃得慢,但一口是一口。旁边几个年轻姑娘叽叽喳喳说新来的男同事,
说他长得周正,就是鞋湿了难看。那女的抬头看了一眼芮啸天,没笑,也没躲,就那么看着。
芮啸天被看得不自在,低头扒饭。饭有点硬,硌牙。后来他知道,那女的是秦芳舒,
秦明远的女儿,在社区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人说她傻,也有人说她善。
有人说她三十多了还不结婚,是挑。有人说她挑什么挑,她爸死了背一身债,谁敢娶?
芮啸天没想这些。他只记得那双眼睛——不亮,也不暗,就像一盏没开全的灯,
但你不觉得它会灭。那天晚上他加班,快十点才走。路过社区图书馆,发现灯还亮着。
他推门进去,秦芳舒在整理书架,听见动静回头:“还没走?”“嗯。”“雨停了。”“嗯。
”两人站那儿,没话。最后是秦芳舒说:“你鞋湿了。”芮啸天低头看,鞋是干了,但皱了,
像老树皮。他说:“嗯。”她从柜台下拿出一双拖鞋:“换上吧,地滑。”他没接。
她说:“不是给你的,是给所有人的。谁湿了脚,都能换。”他这才接过来,换上。
鞋有点大,走起来啪嗒啪嗒响。他走出去,回头看,灯还亮着。他想,这地方真怪,
人都走了,灯还开着。开给谁呢?鬼吗?后来他才知道,那晚图书馆里,有个老头,
阿尔茨海默症,每天晚上九点准时来,说要等他女儿放学。他女儿其实早死了,
死在1997年的一场车祸里。可秦芳舒每晚都等他,给他泡茶,陪他说话,等他说困了,
再送他回家。灯,是为他开的。芮啸天不懂。但他记住了那句话:“永远不要吹灭别人的灯。
”他不知道这灯是谁的,也不知道它为啥不灭。但他知道,从那天起,他鞋里进了水,
心里也进了点啥。说不清,道不明,就像那盏灯,不亮堂,但也不灭。
第二章 心灯未明芮啸天在文化馆待了三个月,鞋换了两双,心没换。他这人心硬,
不是天生的,是让生活一脚一脚踹出来的。老家在豫北一个叫王家屯的地方,爹是泥瓦匠,
娘在村口卖煎饼。他上高中时,每周带一罐咸菜,吃七天。有次罐子破了,咸菜撒了一书包,
他坐在教室外头,一粒一粒捡,手指头沾着盐粒,发白。同桌说:“你也不嫌臭。
”他说:“不臭。”其实臭,但饿比臭厉害。后来他考上北大,全村放了鞭炮。
爹把存了十年的酒开了,喝多了,抱着他说:“咱家祖坟冒青烟了。”他没哭,
只觉得那酒味呛人。所以他信一句话:人活着,得靠自己。帮别人?那是有余力才做的事。
他现在还没到有余力的时候。文化馆这地方,看着清闲,其实水深。评个先进,争个项目,
能吵出人命。今年省里有个“基层文化振兴工程”,拨款五十万,谁拿到,谁就是功臣。
李主任盯了好久,天天开会讲“格局”,其实就是想让上面看见他。芮啸天也想要。
他想用这笔钱,做一套“延津非遗影像档案”,名字起得响,还能出书,评职称。他写方案,
熬夜三天,头发一把一把掉。方案交上去,李主任看了,说:“格局可以,但缺亮点。
”亮点在哪儿?在另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叫赵有才,五十多岁,文化馆老职工,编过县志,
懂方言,会唱大平调。他有个外甥在乡下搜集了一堆老戏本,全是手抄的,有百年历史。
赵有才想用这笔钱把这些戏本数字化,建个民间戏曲数据库。芮啸天去他家看过一次。
老房子,墙皮剥落,屋里一股中药味。赵有才坐在小板凳上,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戏本,
边翻边念:“正月里来是新年,家家户户点红灯……”念着念着,眼圈就红了。
芮啸天心想:这人真傻,都什么年代了,谁听这个?但他嘴上说:“赵老师,
您这项目有文化价值。”赵有才高兴了,拿出一包茶叶:“尝尝,自己炒的。”茶是尝了,
方案也被芮啸天“借鉴”了。他把戏本内容揉进自己的影像档案里,
加了一章“民间戏曲活态传承”,图文并茂,还配了二维码,一扫就能听录音。方案交上去,
上面回话:“有创新,有深度,重点考虑。”赵有才还不知道。他还在家一页一页抄戏本,
准备下周汇报。芮啸天也没觉得不对。他想,竞争嘛,谁强谁上。
他芮啸天能做出更大的影响,赵有才顶多修修补补。直到那天晚上,他加班到十一点,
准备回家。路过赵有才办公室,门没关严,透出一线光。他听见里面有人哭,压着嗓子,
像被掐住脖子的猫。他推门进去,赵有才坐在桌前,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
桌上摊着那些戏本,旁边是药瓶和半杯凉水。“赵老师?”芮啸天叫了一声。赵有才抬头,
眼睛红得像熬了三天的驴。他不说啥,只把一张纸推过来。是评审组的内部意见,
还没正式通知,但已经传出来了:赵有才的项目“缺乏系统性,技术手段落后”,不予立项。
芮啸天站着,没说话。赵有才忽然笑了:“小芮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干了三十年文化工作,到头来,连个戏本都保不住。
”他指着那些泛黄的纸页:“这些角儿,唱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连块碑都没有。
我就想让他们留个声,留个影。可现在,连这点念想都没了。
”他声音低下去:“我女儿去年查出白血病,化疗花了三十万。我寻思,要是这项目成了,
能有点补贴,也算……也算对得起她。”他没说完,又低头哭了。芮啸天站在那儿,
像被钉住了。他想起自己那罐咸菜,想起爹喝醉酒抱着他,想起自己在图书馆看见的那盏灯。
他忽然明白,赵有才不是在争钱,是在争一口气,争一盏灯。可他芮啸天,把那盏灯,吹了。
他走出办公室,雨又下了,不大,但能湿鞋。他没带伞,也没跑。就那么走着,
鞋里咕叽咕叽响,像在哭。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黑地里,四面八方都是灯,
一盏一盏,亮着。他走过去,一盏一盏,把它们吹灭。吹着吹着,天全黑了。他蹲下,
抱住头,听见无数人在骂他:“你凭啥吹我的灯?”“我女儿还没好,你凭啥灭我的希望?
”“我爹唱了一辈子戏,你凭啥说它没用?”他惊醒,满身冷汗。窗外天没亮,但有光,
是路灯,照在墙上,像一盏不灭的灯。他爬起来,打开电脑,
删了自己方案里那章“民间戏曲活态传承”。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他知道,
再不这么做,他心里那盏灯,也要灭了。第三章 黑手与光赵有才的项目没批下来,
但文化馆出了件更大的事。社区图书馆要关门了。这消息是李主任在会上说的,轻描淡写,
像在说“今天食堂没豆腐”。“街道办通知,社区图书馆经费砍了,下月底清场。
书能搬的搬,不能搬的,该处理处理。”底下人点头的点头,叹气的叹气,没人说话。
这种事,见多了。一个破图书馆,能有啥用?谁还看书?芮啸天低头扒笔记本,
笔尖戳破了纸。他知道那地方。他知道那盏灯还在亮。散会后他往资料室走,
听见两个小姑娘在水房嘀咕:“听说秦芳舒天天去街道办求人,脸都磨破了。”“求有啥用?
上头说这地要改建成老年活动中心,打麻将的比看书的人多。”“她一个女的,犟啥犟,
认命得了。”“就是,手黑成那样,谁看得起?”芮啸天停下。“手黑?”“哎哟,
吓我一跳。”一个小姑娘从门缝探头,“你没听说啊?秦芳舒她爸以前在化工厂干过,
她小时候帮人洗工服,手沾了染料,洗不掉,一辈子黑乎乎的。啧,看着怪渗人的。
”芮啸天没说话,走了。他想起第一次见秦芳舒,她递拖鞋给他,手伸出来,确实黑,
指节处颜色更深,像沾了煤灰。他当时只觉得粗糙,没多想。现在想,那不是脏,是伤。
他下午没在办公室,去了社区图书馆。秦芳舒在整理书,一摞一摞往纸箱里装。动作很慢,
像在埋人。见他进来,没停手,只说:“来了。”“嗯。”“书得走了,人还得留下。
”芮啸天看着她手,黑的,但稳。他忽然说:“我能帮什么?”秦芳舒抬头,看了他一眼,
像看一个陌生人。“你?”“嗯。”“你不是忙着评先进吗?”芮啸天脸红了。
“那事……不重要了。”秦芳舒没再问,递给他一摞书:“装箱,按编号。
”他们干了一下午。天黑了,灯亮了。那老头又来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穿件旧中山装,
站在门口问:“我女儿放学了吗?”秦芳舒走过去,像哄孩子:“快了,再等会儿。
”她拉他进来,倒茶,找了一本图画书念给他听。老头听着听着,睡着了。芮啸天看着,
心里发堵。这地方要没了,这老头上哪儿听故事去?晚上九点,他送老头回家,秦芳舒锁门。
雨又下了,不大,但能湿鞋。两人站在屋檐下,没伞。芮啸天说:“项目我退出了。
”秦芳舒愣住。“啥?”“赵有才的项目,我退出。我不争了。”秦芳舒看着他,
雨水顺着屋檐滴,一滴一滴,砸在地上。“为啥?”“我吹了别人的灯。
”“……”“我不想再吹了。”秦芳舒没说话,过了好久,才说:“你手干净吗?”“啥?
”“你手干净吗?”她把手伸出来,黑的,“我手是黑的,可我心里不黑。你手白,
心里黑不黑?”芮啸天说不出话。秦芳舒把伞从门缝塞进来,是把旧伞,伞骨断了一根,
用铁丝缠着。“拿着。”“你呢?”“我等雨小点。”他撑伞走,回头望,
图书馆的灯还亮着。秦芳舒站在门口,没躲雨,就那么站着,像一盏不肯灭的灯。第二天,
芮啸天去街道办,找主任。主任姓王,胖,说话带鼻音,像猪哼。“图书馆?早该关了!
一年到头没几个人,白烧电!”芮啸天递上材料:“这是借阅记录,过去一年三千二百人次,
平均每天九人。不多,但都在。”王主任翻都不翻:“九个人?还不够我一顿饭钱!
”“还有社区儿童读书会,每周一次,三年没断。”“那能当饭吃?”“老人来读报,
孩子来写作业,失业的来查资料找工作……”“行了行了!”王主任一拍桌子,
“你是不是收了好处?这么上心?”芮啸天没发火。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是秦芳舒整理的视频截图:孩子们在读书,老人在写字,一个失业青年在电脑前查招聘信息。
“这不是好处,这是光。”“啥?”“这是别人的光。你关了它,不是省电,是灭灯。
”王主任愣了,像听天书。“你神经病吧?”芮啸天走了。他没再去找人,回了文化馆,
打开电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亮》。他没署名,
发在市政务论坛上。文章里写了赵有才,写了秦芳舒,写了那个老头,
写了三千二百个借书的人。他写道:“我们总以为光是有限的,多一盏,就少一盏。
所以有人成功,我们就眼红;有人亮了,我们就想吹。可光不是钱,不是饭,
它是越传越多的东西。你灭一盏灯,黑暗就多一分。你点一盏灯,光明就长一寸。
别吹别人的灯。因为你不知道,那盏灯,正照着谁的命。”文章发出去,没人理。第三天,
有个人转发,是个记者。第四天,本地公众号做了专题。第五天,教育局打电话来问情况。
图书馆没关成。街道办改了主意,说“再研究研究”。芮啸天没告诉秦芳舒是他写的。
他知道,有些事,做了就行,不用说。可有一天,他路过图书馆,听见里面有人念那篇文章。
是秦芳舒的声音,一句一句,像在念经。念完,她对那老头说:“听见没?这世上,
有人记得咱们的灯。”芮啸天站在门外,没进去。雨又下了,但他没湿鞋。
他觉得心里有东西在烧,不烫,但亮。像一盏灯,终于点着了。第四章 一笔写己,
一笔写人秦芳舒这人,话不多,但话都在事里。她每天六点起,先熬一锅小米粥,盛两碗,
一碗放凉,一碗趁热端给隔壁的陈婆婆。陈婆婆八十二,中风瘫了三年,说话漏风,
吃东西总往下掉。秦芳舒就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喂,手稳,眼神也稳。喂完了,
拿湿毛巾擦她嘴,再掖被角,说:“慢点睡,我七点四十回来锁门。”陈婆婆“啊啊”两声,
算答应。她上班不骑车,走路,二十分钟。路上经过一个修车摊,摊主老马,五十多,
瘸一条腿,靠修自行车为生。她每天路过,都问一句:“收摊没?
”老马说:“等最后一个学生娃。”她点点头,走了。其实她可以不走这条路。
但老马的摊子在图书馆后门拐角,她绕过去,等于多走十分钟。可她说:“他等着收摊,
我等着开门,顺路。”别人问她图啥?她说:“图他修我车时,多拧半圈螺丝。
”别人笑她傻。她不辩,只说:“人心是秤,你称他,他也称你。”她手是黑的,洗不掉。
小时候她爸在染料厂,她妈病着,她去帮工,洗工服,一洗三年。十岁那年发高烧,还在洗,
染料渗进皮肤,医生说:“洗不掉了。”她妈哭,她没哭。只说:“那以后我不穿短袖。
”长大后相亲,有人见她手,皱眉:“干啥了?煤窑里挖煤?”她不恼,把手收进袖子,
说:“洗过别人的脏,所以知道干净多贵。”对方走了,再没来。她在图书馆,
书架编号是她自己定的。不按A-B-C,也不按四角号码,按“春、夏、秋、冬”。
春天架上是诗和童话,夏天是小说和游记,秋天是历史和传记,冬天是哲学和死亡。
新来的志愿者问:“这不合规矩。”她说:“规矩是人定的,人心里冷了,书再规整也没用。
”志愿者不懂。她也不解释。有个孩子,八岁,父母离异,跟奶奶过。每到冬天就来图书馆,
专挑“冬天”架上的书看。秦芳舒发现,
他看的全是讲“死”的:《爷爷变成了幽灵》《獾的礼物》《一片叶子落下来》。她没拦,
只在他来时,悄悄在旁边放杯热牛奶。有一天孩子问:“人死了去哪?
”她说:“去你记得他的地方。”孩子又问:“那没人记得呢?”她看着他,
黑手轻轻放在他头上:“我记着你,你就没死。”孩子哭了。她没劝,就让他哭,哭完了,
递上纸巾,说:“明天还来?”孩子点头。她笑:“那你的灯,我就守着。
”芮啸天慢慢知道了这些事。不是听谁说的,是看见的。他发现她擦书架,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一寸不落,像在给谁梳头。她修书,用特制的浆糊,薄纸补破页,
补完了压在玻璃板下,三天不动。她说:“书破了,魂还在。魂不能受潮。
”他问她:“你图啥?”她反问:“你吃饭图啥?”“活着。”“我这也活着。”他不懂。
她也不逼他懂。直到那天,文化馆开年终会,评“先进工作者”。
李主任点名表扬芮啸天:“小芮同志格局大,主动让贤,把项目让给赵有才同志,
体现团结精神!”底下鼓掌。赵有才低头,眼圈红了。会后,
芮啸天在走廊拦住李主任:“我没让贤,我撤方案是因为……”“别解释!
”李主任拍拍他肩,“好事做到底,名声留得住。你这格局,我看好!”芮啸天愣住。
他想说,我不是为名声。可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他知道,有些真话,说出来,反而假了。
他闷闷地走,到图书馆,秦芳舒在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小王子》里的点灯人。
“他每天点灯、熄灯,别人都笑他傻,说星星自己会亮。可点灯人说:‘我的职责是点亮它,
不是等它自己亮。’”孩子们问:“那他累不累?”秦芳舒说:“累。可他看见光,
就不觉得累了。”讲完,她抬头,看见芮啸天。“进来坐。”他不坐,站在门口。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